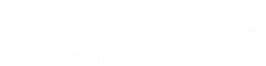這是一個關於四口之家——父母與兩個女兒的故事。最初,大女兒的抑鬱症狀逐漸顯現,在社工轉介下開始接受臨床心理輔導。然而在深入接觸後,我發現不僅是大女兒,這個家庭中的父母和小女兒也同樣深陷情緒困境與抑鬱之苦。
這個家的溫暖,早在十七年前便因父母之間的情感隔閡而逐漸流失。父親因早年不快樂的家庭經歷,長期飽受抑鬱困擾;母親则在生下第二個女兒後,因與丈夫關係疏離而經歷了產後抑鬱。儘管每位成員都深愛這個家,但父母長期的冷戰卻讓家成為了一座無形的情緒牢籠,最終每位家庭成員都深受影響。
幸而透過「重訴我心」輔導計劃的資助,這個家庭得以獲得專業支持,共同面對孩子與自身的抑鬱挑戰。
家庭的艱難歷程
大女兒數年前因抑鬱症開始接受心理輔導。當時,她因情緒嚴重崩潰而無法上學,並極力抗拒留在家中。在輔導過程中,她逐漸學會認識自己的疾病,並開始分辨哪些情緒源自父母的婚姻問題。與此同時,我也與父母進行會談,試圖理解女兒所形容的「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圍。
當時,父母都非常願意接受心理輔導,並坦誠面對他們的困難。他們承認長期的婚姻問題和自身的抑鬱情緒確實影響了女兒。與許多家庭不同的是,這對父母表現出極高的理性與支持態度,努力修復關係並幫助女兒渡過難關。
幾年後,大女兒逐漸康復並重回日常生活。然而,她仍持續關心著家人,並建議我繼續為她的父母和家庭提供支持。果然,在「重訴我心」輔導計劃的支持下,我再次接觸到這個家庭時,發現這次是二女兒出現了抑鬱症狀。
再次來襲來的風暴
二女兒表現出與姐姐當初相似的憂鬱症狀:無法上學、每日失眠、持續感到疲勞與精力耗竭、難以專注學習、情緒低落且缺乏動力,甚至出現自殺念頭。我立即與母親和二女兒會面,協助她們面對抑鬱的挑戰並鼓勵她們尋求精神科醫生的專業幫助。
為何將精神科治療列為優先考量?因為二女兒表現出明顯的抑鬱症狀與自殺意念,需要及時的醫療介入。從神經科學角度來看,抑鬱症與大腦神經傳導物質(如血清素、去甲腎上腺素和多巴胺)的失衡密切相關(Malhi et al., 2018)。抗抑鬱藥物有助調節這些物質的功能。
耐心堅持藥物治療的重要性
然而,藥物治療並非一蹴可幾。許多人因初期副作用或效果不明顯而放棄服藥。根據大規模實證研究(Trivedi et al., 2006),抗抑鬱藥物需要足夠時間才能發揮完整療效。臨床數據顯示,情緒改善通常於服藥後二至四週開始顯現,而要達到最理想的效果,往往需要持續六至十二週的不間斷治療。
這種漸進式改善的生理基礎在於,藥物需持續作用才能引發大腦神經系統的適應性改變,包括調節神經傳導物質平衡與促進神經可塑性。因此,治療師需要持續關注患者的用藥反應,並鼓勵他們在治療初期與醫生保持密切溝通,共同度過可能的適應階段。統計結果明確證實,能耐心堅持完成建議療程的患者,其症狀緩解率與社會功能恢復程度均顯著較高。
問題的核心:夫妻關係中的高牆與孩子的無聲傷痕
在陪伴這個家庭的過程中,我們逐漸觸及問題的核心——一對用「迴避」與「沉默」應對衝突十多年的夫妻。
由於父母最初不願一同前來,我只能透過個別會談,從他們各自的角度,拼湊出這段婚姻如何一步步築起高牆,又如何在不知不覺中,讓兩個最愛的孩子長期沉浸在無聲的情緒鬱結裡。
父親的沉默:來自原生家庭的創傷
父親告訴我,他年輕時就不喜歡說話。原生家庭的創傷讓他長期深陷憂鬱,進入婚姻後,即使對妻子有許多不滿,他也從不表達。「說出來只會更糟」,他這是他從原生家裡意識到的事。久而久之,他築起了一道沉默的牆,將自己與家人隔絕開來,退回到自己的世界中。
母親的孤獨:產後抑鬱與未被看見的付出
母親的敘述則充滿了孤獨與困惑。自從生下第二名女兒後,她感受到丈夫莫名的冷漠與疏離。她不斷自問:「到底我做錯了什麼?」面對丈夫的板臉與不溝通,她早期是不斷求助及求問丈夫, 到最後無奈選擇默默承受,將所有精力投注在照顧孩子與家庭上。她知道丈夫和兩個女兒都深受抑鬱所苦,她告訴自己必須「撐住這個家」,但內心深處早已充滿了無法明狀的傷感、憤怒與無力——因為她自己也快要撐不下去了。
這個家庭讓我深刻體會到:「不處理的衝突」殺傷力往往大於「衝突本身」。夫妻雙方都用自己認為最好的方式保護著家庭(父親用沉默避免衝突,母親用付出維持表面和諧),卻不知這種「迴避型溝通」已成為孩子情緒鬱結的源頭。
情緒安全感理論與看不見的傷痕
在臨床工作中,Cummings & Davies(2010)提出的「情緒安全感理論」(Emotional Security Theory)為女兒們的抑鬱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孩子的憂鬱從來不只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家庭情緒系統失衡的深刻表現。透過大量實證研究,包括實驗室觀察(讓兒童觀看成人爭吵的錄影並記錄其反應)、日記研究和長期追蹤,Cummings & Davies發現:兒童天生具有在家庭關係中維護情緒安全感的基本動機。當父母的婚姻衝突(無論是激烈爭吵或冰冷沉默)威脅到這種安全感時,孩子會發展出各種應對策略來試圖恢復家庭穩定。
在這個家庭中,兩姐妹的處境正是如此。女兒曾告訴我:「我最害怕的就是晚餐時間,當爸爸媽媽和我三人坐在一起時,那種沉默讓我窒息。」此外,孩子們不自覺地成為父母之間的「調解者」,總是試著為雙方說話,希望能搭建溝通的橋樑。更讓人心疼的是,當她們發現自己的行為可能引發父母衝突時,會立刻陷入深深的自責。這些努力看似是解決問題的嘗試,但從情緒安全感理論來看,這其實是情緒調節系統長期超載的表現。
對這個家庭而言,父母雙方均感到非常吃力與疲憊。媽媽認為問題的核心在於與丈夫之間的關係,若無法正視並處理夫妻間長期存在的溝通與情感問題,則難以真正緩解家庭整體的壓力。
關鍵問題在於,媽媽長期感受到丈夫的冷漠與迴避。自多年前生育孩子後,她經歷了產後抑鬱,而多年來心中積壓了許多難以排解的情緒。這些未被處理的情緒,如同隱藏在家庭背景中的「情緒地雷」,不時爆發,女兒們看在眼裡,內心既難過又無所適從,承受著巨大的心理負擔孩子長期處於父母不和的家庭環境中,容易出現各種身心症狀,心理狀態容易陷入混亂與不安。
臨床心理學家的介入與反思
A. 重建個人及家庭的情緒安全感
作為治療師, 面對長期情感冰封的夫妻關係,我意識到一個關鍵事實:直接觸碰核心問題,可能對整個家庭造成傷害。
長期回避衝突的夫妻,通常缺乏處理強烈情緒的必要技巧。若在治療過程中強行迫使他們直面最深層的問題,極可能觸發原始的「戰或逃」反應,導致溝通完全崩潰,使整個家庭陷入「情緒超載」(Emotional Overload)的狀態(Cummings & Davies, 2010)。更令人憂心的是對孩子的潛在影響。若治療過程引發激烈衝突卻未能提供及時修復,孩子目睹的將是更加令人不安的場景。這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會進一步破壞他們的情緒安全感,甚至可能加劇其焦慮與憂鬱症狀(Davies & Martin, 2013)。
因此,治療的首要目標不應是急於解決問題,而是逐步重建個人與家庭的情緒安全感。正如妻子所說,父親很難信任他人和自我表露。然而,在輔導室中,他開放地表達了自己的悲傷和內疚,並非常願意承擔自己的責任來改變家庭氛圍。我意識到每位成員都需要先重建個人的情緒安全感,才能有力量面對家庭系統的困境。
B. 承認限制,聚焦現實目標
我深知這個家庭的經濟狀況有限,若無補助根本難以負擔常規輔導費用。在有限的會面次數中,我的核心挑戰在於:如何有效協助女兒應對抑鬱與壓力,同時支持父母在家庭僵局中逐步前行。我向家人坦誠相告:「我們的時間雖然有限,所以我們要一起商量共同常助你們女兒的方法。」這種對限制的坦誠,反而成為一種力量,有助降低不切實際的期待,讓大家更聚焦於可實現的目標。
我們的核心是讓父母能夠共同支持女兒走過這段起伏不定的康復之路,女兒狀態脆弱多變,父母必須學會合作面對病情起伏,而他們自己也需要被支持,才能更好地扶持女兒。在有限時間內,我致力使家庭成為「情緒安全基地」——療癒起點不是解決所有問題,而是透過示範安全不批判的溝通;其次是緩解父母因女兒抑鬱產生的自責與內疚。
C. 在黑暗中看見光,不被無助感困住
在聆聽家庭成員的故事與困難時,作為治療師,我也深深感受到那種令人動彈不得的無助與窒息。然而,我始終提醒自己:與其追求一步到位的巨大改變,不如以「嬰兒步伐」為目標,在微小的進步中尋找希望。專注於與他們建立安全的連結,並關注他們的進步。我深知,唯有我自己先看見光,才能帶領他人同樣看見光明。因此,我開始轉換視角,重新審視這個家庭:
我看見父母兩人儘管十七年來傷痕累累、難以溝通,卻依然努力守護這個家;
我看見兩個女兒雖然面對父親的冷漠,卻仍能感受到他對她們的關心與體貼;
我看見在這個家庭中成長的孩子,擁有格外優秀的特質——善解人意、在困境中堅持努力、溫文有禮且充滿愛心;
我更看見那位母親,即使多年來被丈夫拒絕,依然深愛著他,並願意理解他的困難與局限。
我將這些觀察和亮點一一反映給父母與女兒,讓他們看見自己與彼此身上那些不曾被注意的光亮。
在最後一次與父親的會談中,我問他在整個治療過程中印象深刻的部份是什麼。他回答說:「原來我的付出是有回報的,原來孩子們是喜歡親近我的。我感受到治療師能夠不偏不倚地理解我們的家庭,我在這裡找到信任,也更想為家人付出更多。」為了讓孩子吃到更健康的食物,他開始在家中下廚;為了及時給予支援,他堅持等到孩子安睡後自己才休息。
母親也告訴我:「多謝你聆聽我,明白我的辛苦,也讓我知道在問題如何行下一步。我是不甘心,也乏力,但我會努力撐下去。」為了讓女兒可以輕鬆一下,更安排了 staycation, 與女兒共度優質時光,一起享受輕鬆的staycation。女兒開心地告訴我,她非常喜歡這樣毫無壓力的放鬆時刻。
D. 不能成為好夫妻,也希望可以成為好父母
在意識到夫妻雙方難以進行相互分享後,我們設定了共同目標:即使不能成為好夫妻,也可以成為好父母。我鼓勵他們參與理解女兒的過程,避免在女兒面前說對方不是而造成三角化,並建議他們尋找可信賴的輔導員或社工繼續支持彼此。
他們其實非常愛護女兒,在女兒被診斷憂鬱症、自己也處於心力交瘁的狀態下,仍努力嘗試維持這個家。因此,我的工作一方面在於幫助他們更清晰地認識孩子的病情,另一方面也承接他們的內疚與傷感,讓這些情緒被看見、被理解,而非立即處理積怨十幾年的歷史問題,這能有效降低防禦和阻力。之後,我各自和父母共同商討如何在目前冰冷疏遠的關係中,找到具體且可行的方法共同付出和投入, 雖然目前他們仍未能完全達成共識、共同面對關係議題,但至少雙方都願意在「做好父母」這個角色上繼續努力,而這也為未來的進展留下了空間與希望。
結語
我由衷感謝這家庭願意敞開心扉,讓我見證並分享個人抑鬱與家庭動態之間深刻的連結,以及照顧者在陪伴孩子面對抑鬱時所經歷的焦慮、自責與無助。願你們繼續每努力, 彼此點亮了前行的路。也衷心感謝資助方的慷慨支持,讓眾多經濟困難的家庭能夠獲得專業心理輔導服務.